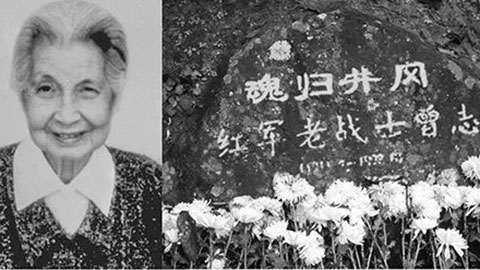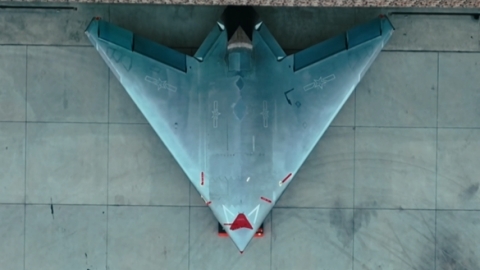在距离哨所下方100多个台阶旁的石坡上,一幅官兵手绘的国旗格外醒目,国旗下方“我在祖国边陲,祖国在我心中”的字样苍劲有力,在夕阳的映照下熠熠生辉,宛如戍边官兵们一颗颗炙热的爱国之心,闪耀着永不磨灭的光芒。
仲夏高原,云雾如絮,缠绵山尖。疾风掠过,阳光刺破云层,西藏山南军分区3197哨所的轮廓,赫然悬于云端。
孤悬绝顶,三面临渊。一条近80度、近乎垂直的石阶路,是它连接外界的唯一通道。这条曾因2187级台阶名冠雪域的“天梯”,镌刻着一代代戍边人用青春、汗水乃至生命书写的忠诚。它连接云端与大地,更通向戍边人心灵的制高点。

天梯铭刻忠诚 岁月见证传承
午后,阳光穿透密林细缝,哨楼旁的苍劲云杉下,三级军士长、哨长邓东城正仔细擦拭一块饱经风霜的木牌。“祖国在我心中”——6个红漆大字在风雨洗礼下虽已斑驳,却在阳光下熠熠生辉。
“它啊,跟哨所的年岁差不多了。”邓东城指尖轻抚粗糙木纹,对新兵罗蓉低语,“字迹会淡,刻在心头的誓言,擦不掉。”这方寸木牌,是哨所扎根绝壁的灵魂印记。
它的根,深扎在英雄的土壤里。20世纪50年代,十八军将士“背着公路”挺进雪域。1951年寒冬,“爆破班”班长张福林在雀儿山排除哑炮,遭遇塌方,年轻的生命被巨石吞噬。次年,他被追授“筑路英雄”,生前所在班命名“张福林班”。
“新兵上哨第一课,必听张福林老班长的故事。”邓东城语气庄重,“他的精神,是‘天梯’最深的根基。”1987年5月,“张福林班”战士将五星红旗插上3197高地,从此扎根于此。
回望来路,荆棘遍布。“那时哪有路?”邓东城翻出泛黄老照片:树枝搭的窝棚,雨季喝泥洼积水;山洪断路,就着雪啃干粮;天梯冲毁,老哨长带人悬吊绝壁抢修……初代戍边人,一手握钢枪守卫疆土,一手挥锹开路,肩挑背扛,硬生生在飞鸟难栖的绝壁凿出立足之地,用一年多血汗,垒起2187级“天梯”。
“守护于此,责任如山。”下士李佰棋抚摸着冰凉的栏杆感叹。如今,简易公路通至半山,台阶减至769级,索道运输让补给时间从两小时缩至一刻钟。哨楼内,地暖驱寒,清泉入户,阳光棚、电网、先进执勤设备一应俱全……物资匮乏已成历史。
巧合的是,李佰棋与“筑路英雄”张福林是一个村的。从小受到了红色熏陶,大学毕业后,他毅然穿上军装,来到张福林生前所在的班,执剑守边固防。“红色基因不是口号,是刻在骨子里的选择。”李佰棋如是说道。
他的笔记本扉页郑重写着:“光荣在于平淡,艰巨在于漫长。”——这句来自电视剧《士兵突击》的台词,成了他扎根边关的精神灯塔。他渴望如“许三多”般,在平凡中绽放光芒。
岁月流转,精神永恒。荣誉室里,“张福林班”的锦旗永远闪亮;新兵第一课,仍是那段峥嵘岁月。“条件好了,但‘张福林班’那股拼劲儿、那份‘什么也不说’的担当,一点都不能丢!”邓东城凝望哨楼顶上的高清摄像头,又回望木牌,铿锵有力地说道,“张福林老班长用命凿路,咱就用心守边!”
青春在云端淬炼 哨位上书写成长
3197哨所的仲夏,浓雾是常客,常将山峦裹得严严实实,能见度不足10米。一代代官兵的青春,便在这弥漫的云雾中淬炼成钢。

连队组织下连新兵攀登“天梯”,前往 3197 哨所。
邓东城是首位在哨所上服役的三级军士长。初来时,他苦练“闻声辨位”——风声呜咽、雪压枝断、野兽踏叶,皆须刻入脑海。一次异响,他扔下地图紧盯雾中,战友刚摸枪,他已摆手:“积雪压松枝,远着呢。”这份在迷雾中练就的本能,是戍边人的看家本领。
如今,浓雾再起,轻点鼠标,监控画面便能切换自如,边境尽在掌握。邓东城盯着屏幕,欣慰中带着一丝怅然:“技术先进了,可站岗放哨的警惕心,不能丢。”
巡逻路上,他总对新兵说:“机器看得清影像,但大山的脾气得用心摸。”他教他们看云识天:“云跑急,暴雪至;云凝滞,阴雨连。”这些用岁月攒下的“通关秘笈”,是无价之宝。
“装备更新,意味着责任更重!”有了新装备,邓东城着手打造哨所“数据库”。他将多年观察所得经验方法整理成册,科学划分监控区域,制订处置流程,加速新兵成长,培养更多“边防通”。
老兵用青春坚守树起标杆,新兵怀揣梦想注入活力。在这片淬火之地,青春正拔节生长。
上等兵康德位透过智能望远镜,目光如炬扫描边境。他的父亲戍边牺牲,母亲难产离世。为此,家人反对他参军,大学毕业后,他却毅然勾选“边远艰苦地区”:“就想离从未谋面的父亲,近些,再近些。”这份情感,化为执勤时超乎年龄的沉稳。
梦想需汗水浇灌。初来时,上等兵梁胜杰是体能堪忧的“小胖墩”,李佰棋、康德位、罗蓉的成绩也刚及格。邓东城如兄长般引领:雷打不动的高原缺氧训练、精心搭配的伙食、背背囊上下山练体能……他冲在前头鼓劲:“坚持!上哨的路就是最好的跑道!”军事技能训练,他则异常严格:“这是边防军人的命根子!”
智能装备操作,手把手教,逐个考核。李佰棋初学望远镜,紧张得手心冒汗,一次考核失利换来两小时“加餐”,终在酸痛中掌握精髓。
汗水浇灌,终见花开:李佰棋获评“四有”优秀士兵并入党;梁胜杰减重50余斤,脱胎换骨;罗蓉3000米跑出12分40秒;康德位成为入党积极分子……青春梦想,在云端哨位璀璨绽放。
这天拂晓,哨音撕裂寂静。“全班注意,迅速对目标区域实施抵近侦察!”邓东城口令清晰洪亮。
浓雾弥漫,能见度不足5米,碎石湿滑。罗蓉紧跟李佰棋,心悬到嗓子眼。“别慌,踩稳,跟紧脚印!”李佰棋声音穿透迷雾。抵近观察点,罗蓉掏望远镜的手被按住:“先听!”几秒后,“沙沙”声传来——是风拂草动。“记着,雾里看不如听,听不如摸地形。”
随后,两人默契配合。抵近、采集、上传,一气呵成。3分钟,信息回传。“报告哨长,任务完成!”罗蓉声音带着微颤的兴奋。
原来,这紧张一幕,是邓东城为罗蓉准备的入哨考核。仪式上,邓东城郑重将望远镜交到罗蓉手中:“列兵罗蓉!接过它,就是接过‘张福林班’的使命!做党和人民放心的忠诚哨兵!”
年轻列兵挺直胸膛,双手接过沉甸甸的使命,誓言激荡山谷:“我定不辱使命!为祖国站好岗,守好边,做祖国最亮的眼睛!”未满一年,站上英雄哨位,罗蓉满怀自豪:“老兵教我装备、识图、适应高原……哨长带我走遍石阶,讲背后故事,让我懂了守护的真谛。”
守边就是守家 孤哨盛开繁花
云端孤哨,寂寞如影。为了给寂静的哨所添一丝生气,官兵们曾收养了流浪狗“铛铛”和猫咪“叮叮”。它们脖子上系着铃铛,跑动时发出“叮叮当当”的声响,曾是哨所里最欢快的音符。
可惜,“铛铛”为了保护厨房,勇斗狗熊时重伤牺牲。此后,“叮叮”成了全哨的珍宝,陪伴官兵们度过了十年岁月,成为哨所里资格最老的“兵”,见证了无数的悲欢离合。
前年年初,“叮叮”走到了生命的尽头,在邓东城的怀里安静离去。邓东城默默抱着它坐了一夜,黎明时分,将它安葬在哨所旁。不久后,连长陈怀圣从山下抱回一只新猫,大家仍叫它“叮叮”,让这份温暖得以延续。
哨所深处高山绝壁,却深得动物的青睐。一天深夜,一只大黑熊潜入厨房大肆“扫荡”,连冰箱里的冻品也没放过。第二天清晨,面对一片狼藉的厨房和失踪的电饭煲、食用油,梁胜杰苦中作乐:“熊大这是拿回去给熊二做饭了。”一句话引来一阵无奈的笑声,驱散了些许狼狈。
为了应对黑熊的侵扰,官兵们群策群力,经过仔细观察,总结出狗熊昼伏夜出、怕光怕响的习性特点。于是,邓东城购置了一批鞭炮,把军犬安置在厨房附近。每当狗吠声响起,预示着黑熊的再次降临,官兵们便迅速点燃鞭炮,刹那间,鞭炮声把黑熊吓得落荒而逃。
戍边日久,哨所早已成了大家的家。康德位下山体检,归来时背着大包小裹。战友们以为是美食,打开一看,却是修水管的扳手、剪草皮的剪刀、描红戍边石的刷子、格桑花种子……大家相视无言,心中的敬意油然而生。
以哨为家,是官兵们心照不宣的默契。邓东城为哨所周围的树木竹丛浇水施肥,筑起一道绿色屏障;康德位视每块石头为珍宝,精心在上面刻上强军话语,用以自勉;李佰棋酷爱鲜花,工作之余总会采撷培育,给哨所增添一抹亮色;梁胜杰用镜头记录下这里的每一个欢笑瞬间和坚守时刻。他们用双手,将这云端孤哨打造成了一个温馨而坚韧的家园。

上等兵康德位描红戍边石,汲取精神力量。
星河升腾,云海在脚下翻涌成浪。天梯之上,青春已站成永恒的界碑。他们站的,从来不是冰冷的石头,而是万家灯火里的安宁;他们守的,也绝非孤寂的山巅,而是祖国胸膛上最滚烫的脉搏。正如那副哨楼前的对联所言:
头顶边关月,情系万家圆!
——什么也不说。
文图/李国涛 韩佳皓 张照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