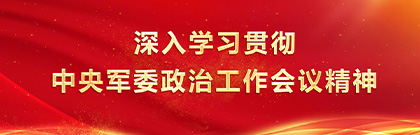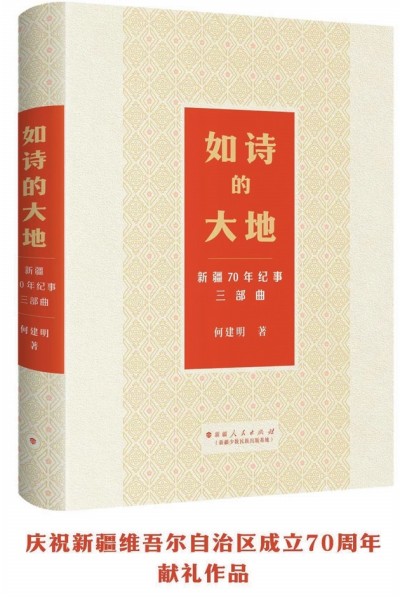
▲《如诗的大地》 何建明著 新疆人民出版社2025年10月出版
在大地上行走,书写如诗的新疆
■中华读书报记者 舒晋瑜
著名报告文学作家、全国报告文学委员会主任何建明曾经对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领导和出版社的同志说:“写这本书,会耗尽我毕生累积的才情与经验。”
是什么书令这位创作了四十余年的老作家从一开始就预判到如此大的难度?
何建明回答说:是《如诗的大地》。他承认自己不止一次提到此书的创作难度。
2025年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70周年。天山南北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大变化,作为献礼之作,《如诗的大地》既是对新疆辉煌成就的深情礼赞,也是向世界展示真实、立体、全面新疆的重要窗口。
“在我写作人生中,可能不会遇到比新疆更难写和更大的题材了!”但是收官之后,他同样承认,自己收获是最大的。不仅仅是这部书本身。写完这本书,不仅仅是对新疆的认识有了全新的感受,更重要的是获得了更多的创作灵感和素材,它们足够何建明为未来的“新疆写作”提供动力和基础——新疆题材将是他创作的一个重要源泉和闪光点。
一、都是新疆最值得书写的精美时代画卷
中华读书报:先是《石榴花开》,又写《如诗的大地》。为什么您和新疆这么有缘? 对比前作《石榴花开》,您在本书的创作视角上有何变化?
何建明:是的。我认为,新疆题材的写作,对每一个作家而言都具有强大的吸引力,因为新疆大而美,同时充满神秘,且至今仍有许多尚未揭秘的东西,所以从当代文学而言,我认为真正的新疆大书写没有开始,尽管我们看到也有新疆的作家所写的作品,现在很受关注,但那一类写作我称之为仍然属于新疆题材中的“小我写作”,并非“大新疆”书写。所以在现代化汹涌澎湃前行状态下的“大新疆”书写,其实只是开了一个头。我的《石榴花开》写的是新疆民族团结问题,这算是接触到新疆大题材的一个方面。也正是这个原因,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70周年之际,新疆的领导同志便把重要的“献礼书”任务交给了我……
《如诗的大地》与《石榴花开》两书在创作上有很大不同。后者是新疆的一个重要侧面,前者是整个新疆和70年的新疆,宏大得多。用一个比喻:后者是对一块“玉石”的精细雕刻和展示。前者则是一幅锦绣河山画,需要史诗般的鸿篇巨著架构和波澜壮阔的书写与阐述。它们虽然主题和内容的开掘程度不一样,但都是新疆最值得书写的精美时代画卷。
中华读书报:《如诗的大地》果然“如诗”。打开看来,满眼的诗意芬芳。从题目到内容,如写可可托海,“可可托海最美的并不只是那几个湖,还有那些峡谷,那些仿佛向你头顶压过来的大山之间的峡谷……它们时而窄得连人的一个身子都挤不过去,时而又如黑云压阵间开出一片天门般开阔无比……”而这些,只是为额尔齐斯河的出场铺垫。这些优美的文字如诗如画,读来朗朗上口,而且引用了包括艾青、王洛宾等在内的大量与新疆有关的诗与歌。似乎这是您最讲究语言的一部作品,不知我的阅读印象是否准确?
何建明:谢谢你认真阅读,并真的是读出了我想表达的“文体之美”“新疆之美”和“内容之美”的三个预设要求。事实上,关于当下的报告文学,很多读者不满意,就是因为不美。这不美,包括了文字、结构和故事等方面。另一方面,我也有深切体会,因为大家对报告文学有了这种“偏见”,所以“凡报告文学,都不美”也在一些读者的意识中比较顽固地存在,因此有优秀的报告文学他们也不太读,自觉不自觉地形成了一种观念。我每次创作时,都想力图改变一下现实的这种局面,包括这一次对新疆的书写。
我在写《石榴花开》时,就有一个观点:写新疆,必须写得美;写新疆,必须写好美;写新疆的美,既要写新疆的自然之美,更要写新疆的发展变化之美和人的精神行动之美。这部《如诗的大地》更多了一个要求:一定要写新疆的历史和岁月之美,因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70年经历了人间沧桑中最重要、最伟大的变迁,可以用“一步跨千年”来形容——我在采访和调研中,看到的这类“一步跨千年”的新疆故事太多、太震撼,也美不胜收! 所以从书名,到结构,到开篇,到每一部之间的逻辑关系、每一部所包含的内容之间的张力与故事之间的递进关系,都比较讲究。而且同样是写一个湖、一座山、一片草原和茫茫大沙漠时,除了直接对自然物景的描写之外,更多的是为想表达的中心内容作铺垫和“起调”,就像一首歌曲的“前奏”一样,后面的“中段”和“高潮”部分,才是根本! 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我希望新疆的作品,必须与新疆的民族特性和那里的“风格”形成一致性。那是个“能歌善舞”之乡,我们的文字和故事,也应当是节奏感强,诗性和诗意的文字要作适度的烘托……你很了不起,已经发现了这一点。我粗略算了一下,整个作品中大约有两万字是散文式文字和诗性语言。我把这视为“如诗大地”非常养眼的“光泽”,希望读者在阅读动人的故事时,获得抒情般的环境美感,能像读艾青的诗、听王洛宾和刀郎的歌一样愉悦。
二、把广阔无限的世界微缩成精美的内容
中华读书报:整部书的结构大气,分史篇、诗篇、史诗篇三部,各部又分宝藏、天路、疆土等章,大章下又细分若干独立且逻辑严密的小章节——听说您是花了一个春节长假的时间来架构?
何建明:这部新疆题材的作品,我称其为我创作史上前所未有的“大书”。作为一部大书,它就必须超越所有中、小作品和一般意义上的大作品。因为题材之大、时间跨度之长、内容之多、涉及层面之广,都是少有的。如果按通常的构思,很难完成。所以一定要打破以往其他作品的那种架构。用通俗的话说,这本关于新疆的书是几部大作品的工程,其复杂性、工程量也是一般意义上几部作品的总和。比如新疆兵团是少不了的“新疆内容”。仅此一块,据知在我写新疆这部书之前,兵团就组织了一批作家写了七八部书,共计150万字。然而在我的这部书中,兵团内容的容量也就是四五万字。可你又不能丢掉一些重要的内容、重要的事件和精神。等于说要把上百万、数百万字的内容,浓缩成我这部关于新疆的大书中的几万字,可采访和调研又不能减少。这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难题。
而我这部大书,需要把整个新疆方方面面的内容都尽可能地包含进去,也就是说,要把一个宽广无限的世界,微缩成一个精美且有相当体量的作品。这种作品的架构,就不再是通常创作一本书的那种“上、中、下”或“开头、中间、收尾”那么简单了!最初的时候,我也感到头痛:到底如何写,如何把内容装进这个“超大的大地”? 最后集中时间,用去了整个春节长假前后共10天时间,反反复复进行推敲贯通,一直到长长地透了一口气为止。现在的《如诗的大地》共设置了“三部曲”,并且每一部都有三个梯次,每一个梯次又有四个章节。这四个章节不仅相互独立,又与同一个梯次中的其他章节串联成递进关系和内在逻辑关系。同时,三个梯次之间既各自独立,又相互关联。比如第一部中“宝藏”“天路”“疆土”,它们之间独立成书都可能成为惊天动地的一部好书。而在《如诗的大地》的一书中,它们就组成了气吞山河、波澜壮阔的新疆江山宏阔与伟大的“底色”。这样的布局,就是考虑到它“大书”的特性,以及它的丰富性、精彩性,以及它的“新疆性”。第二、第三部也是如此。如果读者细心的话,会发现《如诗的大地》确实与众不同,具有超乎想象的大结构,具有真正意义上的“史诗”特质。读者会注意到,我将第一部命名为“史篇”,第二部命名为“诗篇”,第三部命名为“史诗篇”。如此巧妙的关联,堪称一绝,我自己也非常满意。

▲采访塔克拉玛干沙漠腹地的“万米深井”现场。
三、就像攀登一座未知的高山
中华读书报: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70年写一部史诗性作品,其丰富性、复杂性和不可预设性……无论从哪方面来说对作家都是一个巨大的挑战。您已经写了40多年,在创作《如诗的大地》时,还感觉有困难吗?
何建明:是的,因为内容太多,多到天一样大、山一样高、沙漠一样广……内容如此广泛,而且时间跨度是70年。特别需要指出的是,新疆的70年与其他地区不一样的是,它的民族性、复杂性、多样性及许多不确定性,是所有其他题材创作不可能遇到的,在这本书中随时、随地都会遇到。如此,这部书所需考虑的“方方面面”因素是其他书不用担心的,而在这部书的创作中,这些因素几乎随时可能出现。当你弄明白之后,才可能找到合适的采访和创作角度。再一个就是新疆“方方面面”的每一个点,都足以让你付出巨大的代价。特别要说明的是,写“新疆史”的体量之大,新疆的面积本身占全国面积的六分之一,相当于欧洲好几个国家的体量。通常我们写一部二三十万字的书,需要采访一两个月。那么关于新疆题材的采访量应该是五六倍吧! 更难的是,新疆的地域面积又是一般题材的五六倍,一个农业问题、一个兵团问题、一个自然环境问题,你得从南到北走一趟,至少花一个星期……如此加起来,写这本关于新疆的书的工作量是写其他作品的十倍以上。但我根本不可能有这么多时间去完成新疆的采访和调研,而且自治区有关部门当时给我的时间就一年。一年中你要完成采访和写作,这中间的艰辛和劳累,只有我自己知道。就像攀登一座自己心里都没底的高山、穿越从未去过的大沙漠,你并不知道是否能成功,但你必须实现人们的预期。这就是难题。
再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每一次我们的采访日程都安排得自以为很好,结果一出去就会发现,完全不是那么回事。多少次,从一个采访点到另一个采访点,之间的路程,你想象不到它有多远。好几次,我们是在深夜十一二点钟才赶到目的地,必须打着灯去敲人家的家门。等采访结束后已经快到天亮了……这就是新疆,完全与众不同的境况,随时会出现你想不到的事儿。有一次在塔克拉玛干沙漠腹地去看光伏基地。当时的场面太震撼了! 我很想看看光伏发电的原理,基地工程师告诉我,这得上他们的“楼顶”去才能看得到。楼顶多高? 他们告诉我大约六层。我想应该可以上去看一看,六层嘛! 因为电梯没有安装好,所以只能走楼梯。想不到的是,每一层的高度,远远超出一般楼层。等走到四层的时候,我感觉自己的心脏有点扛不住了……最后停停歇歇,总算到了六层。再从六层走下来后,内心确实有些紧张,因为我曾经在野外采访遇到过血压猛增的危险。这一次参观光伏又是一次临险经历,至今想来仍有余悸。在大沙漠里吃沙、在天山的冰雪中受冻……也就不在话下了。以我这样一把年纪的人,也算是很不容易了! 我曾对出版社的同志说:写新疆,真的差点奉献了半条“小命”。
这还只是皮肉之苦。真正创作的困难就更多了:比如说你想要的材料未必能采访到,你想去的地方未必能走得到,你想放进的内容和故事未必能放进去等等,都是写其他书不太会遇到的问题。
还有一件事:为了了解新疆的历史、自然和现实社会等等方面,所以除了多跑、多采访之外,光从新疆图书馆和出版社等借的图书共运回了12箱之多! 这些资料我都得“瞄”一遍。你想想多大的工程量?!
文字和故事架构,也是件少有的难事:你得像建一座“摩天大厦”一样,不知有多少层才算是“完工”……这都是创作这部书中经历的事。当然,后面“审稿”的过程就不去说了,想象不到的事,几乎都出现过。
我想指出一个问题是:有的人一辈子钻在书堆里,靠“啃”前人的书、别人的书而成了“作家”,成了“名人”。搞报告文学不行,我们只能用双脚去“啃”大地,当然我们也“啃”书,但绝对不会是靠“啃”书吃饭。所以我们的创作如果说接地气,那是绝对的和毫无疑问的。
四、“写新疆必须写得美”
中华读书报:关于新疆的作品也有很多。如何在自治区成立70年的时间节点上把新疆这个“好地方”全面呈现出来,写作技巧上也需要考虑周全。您是如何把握的?您觉得《如诗的大地》有哪些特点?
何建明:所谓“好”,其实有几个层面:一是新疆人认为的“好”,这是客观层面;第二个是基层的“好”,这是国家层面和时代层面的;第三个是我作为作家的独立判断的“好”;再者是读者可能感兴趣的“好”。这几个层面都不同,都必须考虑进去,舍掉哪一个,都可能无法完成这部作品,也称不上是“好作品”。因此难也难在这里。所以我在写的时候,既要选择那些新疆人认为的“好地方”“好事情”“好人物”,但也不能全部搬进去。要选择那些与国家大局、时代大局相关、能放在中国甚至世界层面认为的“好”。这就比简单的新疆人所说的“好”的概念要大而深刻。作家要有自己的审美与判断,这是考验一个作家的政治意识、大局意识、社会意识甚至于世界的、国际的意识。除此,最后落脚点要在本书是不是能够让广大读者喜欢的层面上。这个读者是个大概念,它不仅仅是文学爱好者,有相当一部分是领导者、管理者,还有研究者、企业家、投资者。当然普通读者和对新疆感兴趣的人,都是我要考虑的“对象”。所以,这样一来,你的创作就会有很多因素注入文字甚至是结构、标题、故事编排等等方面。
这方面我在分“部”、分“篇章”里,都考虑到了,所以才有了一些很能吸引人的如“宝藏”“天路”“原野”“信仰”“牧歌”等等“大序篇”。如一些非常讲究的故事性和艺术性的章节标题。又如“‘牧羊人’的故事”“只属于可可托海的经典”“葡萄熟了,姑娘去了哪里?”等等,都是很具有可读性、可观性的标题。
另一个特点是:在这书中的文字,至少有一两万字,我认为可以称之为“纯粹的散文”和“诗性语言”。我在创作前就预设了“写新疆必须写得美”“写好美”的考虑,而且在50多万字的整部作品里,我用不少歌曲、诗词在其中。这个目的是加强作品整体内容的节奏感,同时也一直有个考虑:新疆是个能歌善舞的民族,我的作品篇幅很长,中间得有“喘气”的空隙,歌词、诗词放入其中,作用就如这样的“喘气”与“水蜜桃”让它更具“新疆味儿”。

▲在昆仑山脚下。
五、“我死了后,一定将我埋在新疆”
中华读书报:不论是《石河子记忆》中所涉及的刘守仁、陈学庚、尹飞虎这些在戈壁沙漠的贫瘠土地上土生土长的科学家、技术人员、普通军垦战士,还是那些在他们背后默默奉献的千千万万兵团官兵,您都饱含了深情甚至是激情。看得出来,您的写作倾入全部的心血。在采写过程中,是不是有特别多值得分享的感受?
何建明:是。这与我自己的军人出身有关系。“天路”部分投入了我很浓、很深的“军人情结”。在新疆和平解放和保卫新疆的阶段,包括兵团几十年中,军人对新疆的发展与稳定所起的作用,可以说与天山一般巨大、与昆仑一样巍峨。其精神感天动地,催人泪下。单说独库公路:当年我所在的部队为筑这条路,前后牺牲了两百多人。现在我的一位战友在那里为牺牲的战友守墓就已经50年了! 他的儿子也在继承父亲的事业。他们的无私和牺牲精神和令人感动的事情,在南疆、北疆比比皆是。即使是现在,我们很多官兵在昆仑山上守护边疆也是非常艰苦的,高原反应不是一般人能过得了关的,牺牲依然还会经常发生。这些艰苦奋斗和英勇牺牲的事迹,在新疆随处可闻。不用说,数百万兵团人,他们一代又一代人在沙漠戈壁垦荒种地,守护边疆,其事其人,你听后、见之怎可能不动心? 我第一次去采访一个老英雄时,最让我感动的是他的老伴。如今这位叫“刘京好”的老太太年近80,当年到新疆前是刚同她丈夫结婚的山东小媳妇。夫妻俩在边疆线上守护了60多年,在那里生下3个孩子。现在我到他们家看到的景象,都感觉“这日子怎么过的”? 几十年前他们刚过去,就住在沙地下的“地窑子”。白天丈夫骑着马去守边境线,女人一个人在家种地养孩子,风沙、暴雪一来,她只能独守地窑子,其苦到底有多少、多深,只有她自己知道。我去她家里,看到的是一位腰杆弯到90度的满头白发的老太太……我心里极其难受。你说我不写这样的普通人、这样的中国人,我还写什么呢?
如此生动感人的故事,整部书中很多。在石河子采访时,他们给我找了几位老兵。还没有跟他们说什么,一见到他们,一与他们握手,内心就充满了敬意和感动。因为从他们的双手、从他们的双眼、从他们的双腿,可以看到他们曾经经历的岁月——有的人双腿是站不直的,有的人双眼已经看不清了,几乎所有“老兵”的脸庞都挂着沧桑……然而他们一直默默无闻为我们坚守着那片美丽而辽阔的疆土。几位老科学家一生奉献在那里,当他们年迈之后,便会吩咐后代:我死了后,一定将我埋在新疆……这是他们最后的奉献。
将生命和精神一起留在新疆,这是兵团人、守护天山和边疆的军人们、支边人的共同夙愿。
他们就是当代新疆的“精神心灵史”——《如诗的大地》从某种意义讲,就是这样的一部作品。
六、要呈现“他”的精神光芒
中华读书报:9天7000公里北疆行和深夜十一二点敲门采访,这种极端工作方式对素材获取有何独特价值? 是否有未被写进书中的“遗憾的故事”?
何建明:因为新疆太大。有些地方只可能一生去一次,别说采访了! 见一位老边防、老兵团人,你可能不会有第二次机会。所以一旦确定需要采访某一个有意义的采访对象时,你就得尽量“完成任务”,否则就是遗憾! 这也是这部作品的难点之一。失去的,将永远失去。获得的,将永远是宝贵的。所以必须实现极端的可能。把“尽可能”作为工作任务,是我本书创作的一个原则。这种创作在其他文体中是不可能有的。报告文学有的时候就是一场战斗,甚至是一场生死卓绝的战斗。
失去了机会就是最大的遗憾。一位优秀和杰出的报告文学作家甚至宁可牺牲自己的一切,也要获得宝贵素材的道理也在于此。一个好的素材,有时会奠定一部作品优秀的基础。
中华读书报:在兵团、在新疆,“半边天”是实实在在的,有时甚至超越了男性。《母亲是最美的疆土——女人的故事》中您写了湘女,写了上海知青,写了若干个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女人,她们也是伟大的母亲。您用细腻又深情的笔触写出坚韧与伟大的女性群像。您写的人物故事特别生动,人物形象跃然纸上,呼之欲出,能谈谈您在人物刻画上的经验吗?
何建明:写人、写人物故事,永远是文学最重要的任务。报告文学也是如此。我很头痛现在有一些写作者通常很注重“题材”而不注意内容,尤其是内容中看不到“人”,不写“人的故事”,只讲“事”,空洞的事。看一个作家功力如何,常常是体现在看他会不会把一个普通人的普通事,写得生动、精彩而又实事求是,不虚不假,这是报告文学的基本要求,也是最难的事。我是一直比较注重写人、写人的故事,而且尽可能地把人写“活”,这个“活”首先是要真人真事,其次是让真人真事“活”得自然、合理、独特、出彩,再者是要呈现“他”的精神光芒。
中华读书报:《葡萄熟了,姑娘去了哪里?》故事一波三折,写了20世纪70年代吴明珠的“甜蜜事业”做到了国家领导人招待美国总统的餐桌上。这一章从题目到内容都很有悬念,对话和场景都很有现场感、画面感。您很早就将蒙太奇的手法引用到报告文学写作,在这次的创作中更是各种文学手法融入,十八般武艺让人看得眼花缭乱。
何建明:《如诗的大地》一书中的这一章,写的是两位女科学家的故事。她们都是给我们带来“甜蜜事业”的农业专家,一个种葡萄,一个种西瓜,而且影响巨大,改变了新疆甚至全国人民的口味。过去我们只知道葡萄好吃、西瓜好吃,却不知是谁让西瓜和葡萄这么好吃。当我采访完两位女科学家后,才知道了这一切。最让我感动的是,她们都是如此热爱自己的事业,在极其艰辛的条件下,几十年如一日地进行科学攻关,最终谱写了自己精彩的人生和科学事业。这种情况常常让我难以忘怀。写这样的人物,我比较注重“情”字,因为她们身上,就是一个“情”字精神,“情”字光芒。执着、朴素、有爱,是她们身上最宝贵的东西。她们是科学家,同时又是女人、妻子、母亲,这三种身份,使得她们在从事的事业上更加充满爱意,所以成功之后她们也从不骄傲,因为就像她们生孩子一样自然。这一点,是女人或者说女科学家的伟大之处。
跟这样的主人公在一起,就会产生“情”与“妙笔”,因此会写得更好些。我喜欢在这种平和接触中的真实,这种真实是最有“情”景的。
中华读书报:《老兵的风骨——守望“三八线”》很吸引我,您本人就是老兵,如何写出兵团人的特质,是否更有把握?
何建明:“老兵”写老兵,是感情的自然流露,肯定会写得不一般。到南疆后,听到、看到许多老兵的故事,这是我在新疆收获很大的一块。“老兵精神”是受到习近平总书记表扬的,在新疆很有影响,也是新疆兵团和新疆人民的光荣传统。这一块以前听说过,但去以后所看到的和感受到的不太一样。一是新疆的“老兵”风骨,从南到北、从东到西、里里外外,每一个人身上都似乎透着一种老兵精神。这是新疆人的重要精神架构,是钢铁精神,是边防精神,是疆土精神,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精神,也是时代最强音之一。当时我就觉得写这部大书时必须把这一部分内容写进去。老兵们太不容易,他们的牺牲精神、坚守精神、艰苦奋斗精神和教育后代的精神,都是今天我们要好好学习的。任何时候都不能忘却这种精神。他们是耸立在大地上的丰碑,是永恒的民族精神,也是《如诗的大地》上最闪耀光芒的部分之一。
中华读书报:您写到了赛里木湖生态、喀什古城改造等,在如何体现您所追求的“大开大合”和“超然之美”等方面,您做出怎样的努力?
何建明:这部分创作是要下真本事的,既有生动性、文字的美感、散文式和诗性的表达,又必须有创造性——因为这部分内容,读者们见的其他文字太多,而且都是些美文式的游记、散文、诗歌,甚至是影视画面了,你写得不美,谁看? 所以它具有挑战性,文学和文字的挑战。因此必须调动尽可能的知识、经验和创造力。
其实,这得借助你深入生活的一面。你得比旅游者更细腻地去感受自然、体会自然,最后是提炼精彩。
你要成为一名当地的“管理者”,好把控对生态的认识和认知,最后以欣赏和赞成者的姿态去做出自己的正确判断。
你当然还应当成为一名哲学家,以一分为二的辩证思维从政治家的高度来认识新疆的生态文明和保护自然的意义。
最后是文学家的出场:文字之美、艺术之美,是我们文本呈现的形式。它将决定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