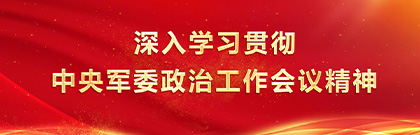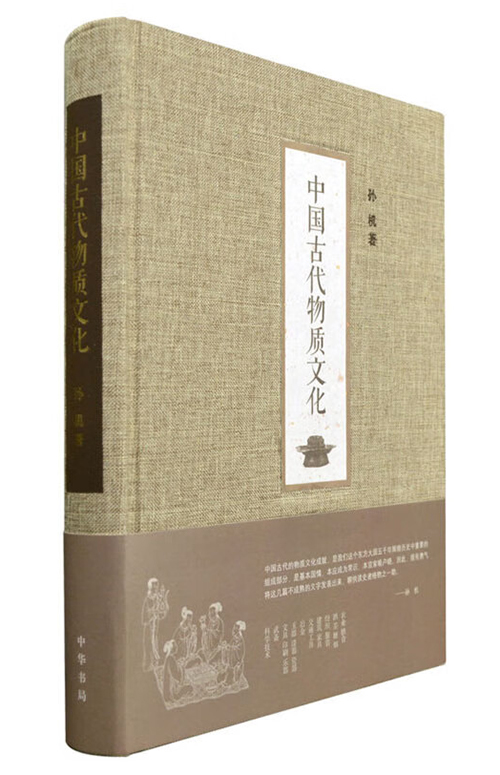
《中国古代物质文化》:
咱们的历史,就在这些物件里
■熊建
孙机的《中国古代物质文化》体大思精,考证精审,是了解中国古代日常生活的利器。其写作缘起是一次闲聊。
一个年轻人跟孙机说,我看古代没有什么不得了的,四大发明不就是放了个炮仗、造了张纸吗?这话震动了孙机。作为中国国家博物馆的科研人员,他深知中国古代物质文化的深厚和绵长,绝非一两句话就能概括,更不可轻视。
李约瑟总结出来四大发明,对于提升中国物质文明、传统文化的知名度和美誉度,有很大帮助,已经成为科技传播领域的常识了。但这种标签化传播很容易造成一叶障目,不见泰山,大树底下不长草。四大发明之外,中国古代物质文化还有相当丰富的内容和层次。不然,古人简直没法生存,张不开口、迈不开腿,不可想象。
全书分为10个章节,古人的衣食住行、柴米油盐,无不涉及;纺织服装、冶金武备,全都包括;文房四宝、瓷器玉器,娓娓道来。这些领域背后的科学技术,也都讲深讲透。可以说,孙机让这些沉默的器物集体开口说话,告诉读者,古代中国人是如何生产生活的。
谈古代物质文化,离不开科技;谈科技,又离不开计算。计算负责处理数量关系,是科技活动的基础。因此,《中国古代物质文化》中专门谈到了与计算有关的器物——算盘。在电脑出现之前,这是一种构造极简单而效率奇高的计算器。
记得20世纪90年代,我上小学还要学习打算盘,什么一退六二五之类的。时至今日,“如意算盘”这个词虽然还在用,但是会打算盘的人,或者说需要使用算盘的场景怕是寥寥无几了,顶多在开发智力、预防衰老这方面出现。
事实上,算盘、珠算背后,蕴含着深厚的文化意义,这是成就今天中国人思维方式的诸多来源之一,我们不能因为学会开车就忘了怎么走路。传统文化是我们的根底,以珠算为代表的算学文化也是成就中国文化基因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可以不用,但应该记住它,别留下遗珠之恨。
珠算是在筹算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筹算是中国最古老的计算方法。筹算,以筹来算,筹是专门为计算制造的竹木或骨制的小棍,也叫策。司马迁在《史记·留侯世家》中说,张良是刘邦的“画策臣”,他就是用这种小棍给刘邦计算。有一次没带正式的算筹,他就拿筷子给刘邦摆。今天我们说的“定计”“决策”“运筹”,都是来自古代的计算活动。
古人讲计算,《孙子兵法》最深刻,开篇即是《计》篇,文中的原话是“庙算”,指在国君议事的地方拿小棍进行计算,计算什么?打仗的敌我力量对比。“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左传》),可以说,“算”在中国历史上居于非常重要的地位,仅次于祭祀。
后来珠代替筹,成为珠算。在民间,老百姓过日子,柴米油盐酱醋茶,离不开算计。如果开个小买卖,要算账、记账,珠算更是大有用场。而且在日常表达中,算盘也有用武之地。孙机举例说,元代陶宗仪《南村辍耕录》里拿算盘打比方:“凡纳婢仆,初来时曰‘擂盘珠’,言不拨自动。稍久曰‘算盘珠’,言拨之则动。既久曰‘佛顶珠’,言终日凝然,虽拨亦不动。”这段话虽然充满歧视佣工的心理,但说明算盘在当时已经是常见之物。
所以说,就这么一个算盘,就能从古籍找到这么多故事,就能发现,这么多领域与算盘、与计算有联系。我们今天脱口而出的“算计”,就是延续了几千年的文化。
孙机的写作,充满辩证思维。他指出,筹算和珠算只求快捷,不留算草,不留过程,以至于抽象化的数学语言在中国始终未能充分发展,这是不足之处。这个论断很有见地,但他没有摊开讲。如果感兴趣,可以看相关科技哲学著作。
《中国古代物质文化》对宏大叙事不感兴趣,提供了另一种历史维度——从器物的棱角触摸时代的温度。它像一份文明的实物清单。告诉我们:华夏文明不仅写在典籍里,更熔铸在每一件炊具、每一匹绢帛、每一架牛车之中。读毕掩卷,忽觉日常器物皆成史书。手中的茶碗、古建的砖瓦,俱有千年故事在沉吟。这或是孙机先生最深远的馈赠——让我们在物质中看见精神,在平凡处发现辉煌。咱们的历史,就在这些物件里。